評論藝術的人醜態百出
網絡世界是個揭露人心的平台,人們不知不覺會大談個人喜惡和品味,暢談對人和事的看法,更會互相貶低對方的價值觀,好像喜歡一個人、一件物品,彷彿有一套絕對真理。
最近,傳媒報導荷蘭某「整蠱節目」 主持,將價值只有$83港元的油畫,放在阿納姆現代藝術館,聲稱是著名畫家 IKE Andrews 的作品。在二十名參觀者中,只有一位稍為猶豫,詢問主持人油畫會否在廉價店舖出售?其餘受訪者,不少將油畫的價值高估一千倍以上,更有人聲稱若油畫只賣二千萬港元,便會買下它;當然,也少不了一些人大發評論後,知道真相深感羞辱。
如果你草率認為大眾不懂藝術,亂評亂估實屬「人之常情」,那麼《香醇的紅酒比較貴,還是昂貴的紅酒比較香?(How Pleasure Works: the New Science of Why We Like What We Like)》的作者 — 保羅.布倫(Paul Bloom)對人心喜惡的研究,肯定會令你連番驚異。[註一]
布倫讓我們重溫荷蘭畫家哈恩.范.米格倫(H. A. Meegeren)的故事。米格倫偽畫了名畫家維梅爾(Vermeer)的作品〈以馬忤斯的晚餐〉,令當時一些評論維梅爾藝術的權威「出醜」,更有人對膺品驚嘆說:「我要強調這是維梅爾的傑作 」。當真相大白後,許多藝評家紛紛收回自己的評價,也有事後孔明的「專家」狠批米格倫作品醜陋,根本不像出自維梅爾之手﹗
藝術如此,音樂亦然。2007年1月12日,在華盛頓特區地鐵站,有人身穿牛仔褲、頭戴棒球帽,手拿一把小提琴,用了四十三分鐘演奏了六首古典音樂,期間一千多人與他擦身而過,只有零星的聽眾丟下合共$32美元的硬幣,以示支持。此人,其實是世界頂尖小提琴演奏家之一:約夏.貝爾(Joshua Bell)。他手上的小提琴價值三百五十萬美元,這場演奏,是他參與評估大眾品味的實驗,可惜實驗結果令他心碎。原來,大眾買貴價票走進音樂廳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演奏出絕妙的音樂,卻是一種氣氛、一種感覺,可是你問買票的人,十之八九還是標榜自己能分辨出優秀/差劣音樂的高尚品味。[註二]
這些經典事例,並非表示世上不存在懂得純粹欣賞好作品的人,倒是強調:我們喜歡/討厭一件事物,究竟是甚麼強烈影響著我們?
幾歲小孩也拜偶像?
一項小孩評估價值的實驗,可謂道出了箇中端倪。布倫親自進行實驗,找來一批6歲大小孩,他們在現場見證過女皇伊莉莎白二世訪問布里斯托(Bristol)的情境,意義在於,確定小孩知道女皇是誰,而且感受過她即場的影響力。
事後,布倫說服了一組6歲小孩,相信眼前有個神奇複製機器,機器一響,B盒子便能複製原來A盒子的那件東西。實驗人員在小孩面前複製女皇曾擁有的酒杯、湯匙,給予他們籌碼,並要求估算「女皇物」(女皇曾擁有)和「複製品」價值分別多少。結果,這組小孩一致將更多籌碼分配在「女皇物」之上,認為女皇碰過的東西有較高價值;然而,另一組小孩沒聽說某東西曾是女皇擁有,他們分配兩件物品的籌碼完全一樣。
更甚,布倫的同事法蘭克.凱爾(Frank Keil)的研究發現,讓孩童觀看一系列得意的照片,例如將一隻豪豬改變成仙人掌,或一隻老虎披著獅子皮,無論牠們的外型如何改變,孩童不會承認牠們真的變了,堅決認為:豪豬仍是豪豬,老虎仍是老虎。唯一例外的情況,若是你以照片顯示牠們連內臟都轉變了,他們才會認為那隻動物真的變了(變質了)。這就是人類對外物特殊的思維:「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我們自小就認定,一件東西之所以「是」那件東西,就是內在含有一些不變的本質。
現在,我們終於對人心喜惡的法則,有了較確切的看法。從小到大,人們深深喜歡的東西,是內心一種投射和聯想,相信那東西與「誰」有關係,是否名人碰過,這些物品的「來歷」對我們的喜惡,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即使一件事物全無分別,但只要它被崇敬的人碰過,價值隨即「飛躍」。同一幅畫作,當別人告訴你那是仿製品,並非出於名家之手,你對它的熱愛頓時消失。我們迷戀的,往往不是物品的外形,或構成它的粒子序列,卻是伴隨物品的「歷史」(誰人碰過、出自誰的手筆),這才成為價值高低的「本質」,我們會將情感投射進物品當中,對它深深著迷。
有人愛儲糞便、偷陰莖,跟暢銷作家做愛?
假如你依然對此懷疑,認為音樂藝術,甚或酒杯湯匙,總有它們令人喜歡的特質吧?說人們主觀認定物品背後的「歷史」,會干預我們的喜惡,真能作準嗎?那麼,我們談談糞便吧﹗ 2002年,泰德美術館(Tate Museum)以數十萬港元買進了一個罐頭,原因只有一個:罐頭內裝滿了藝術家耶羅.曼佐尼(Piero Manzoni)的「糞便」。相信沒有人說,擺在美術館的糞便除了出自藝術家本身,還有何令人喜歡的特質吧?
更有件奇人奇事,希特勒時代以前,曾有位柏林女子公開宣布,她願意跟任何作家做愛,只要那位作家曾賣出兩萬本著作,證明他是暢銷書作家則可。只要一個人深深仰慕拿破崙,即使是位牧師,也會從拿破崙屍體偷偷割下「陰莖」,留為紀念。反過來,當你知道有件毛衣是魔頭「希特勒」曾經穿過,若不能賣錢,你根本不想碰它。[註三] 作者引述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在《創造的行為》(The Act of Creation)的說法,指我們喜愛甚麼,其實像個「勢利鬼」,良好的名譽地位就是我們追逐的本質,如你告訴某位太太,家裏牆上掛著的是畢卡索的真品,之後她也會認定作品「突然」變得更美了。
的確,我們喜歡那個人、那件事物,帶有主觀因素,與我們個人特質、成長經歷密切相關。有些人從事藝術,喜歡一幅畫可以是創作者獨特的用色,他們認定的價值是藝術才能;另一些人若是收藏家,凡社會認定高價值的畫作,價格愈高的畫他愈喜愛;一以貫之,這類人若接受品嚐紅酒測試,必然認為價格愈高的紅酒愈好喝,因為,他喜歡的本質是金錢。如此看來,喜惡心理似乎也相當主觀,難有一貫準則。
迷戀天賦、努力、吃人
事實上,在社會文化和生物演化上,還是有些關於喜惡的共通特質,近年一項研究發現,甚至連獼猴也有人類這種「名位投射」。研究員讓公獼猴在「甜果汁」與「地位崇高公猴的照片」之間作出選擇,獼猴確實會因為崇拜公猴,要牠的照片而放棄美味的甜果汁。
其實,人類鍾情名位之餘,還會喜歡一些普遍特質,譬如喜歡特殊的「努力、天賦、外表、純潔、才能、仁慈(親切)、意志(勇悍)」等等。有研究指,某藝術家同一幅作品,人們被告知他的創作「努力」了26小時,而不是短短的4小時,足以令人們給予作品更高評價。又如被喻為天才的4歲畫家瑪拉.歐姆斯德(Marla Olmstead),當人們在電視特輯之中,發現其父親有指導過她,懷疑作品不是出於純粹的「天賦」,價值隨即急瀉不止。
意志力也是人們崇尚的特質。阿茲特克人(Aztecs)有種習俗,他們會綁住犯人的腰部,再給他武器,讓他有一定反抗,然後一起對他進行「暗角群毆」,直至他倒下為止。隨後,阿茲特克人便吃他的肉,剝他的皮做斗蓬,因為他們相信,吃掉奮戰而死的人,可連帶將「勇悍」的本質吸收在體內,這就喜愛戰士特質的心理投射,反映在他們吃人的文化上。
這樣的心理投射並非罕見。2003年,42歲名叫阿敏.梅委斯(Armin Meiwes)的電腦專家,網上招人讓他吃掉,最後名叫伯恩.布崙迪(Brend Brandes)的男人應約,結果真的遭殺害被梅委斯吃掉。梅委斯最後被問到吃人的原因,他認為吃掉布崙迪後,感覺心態平穩了,也與他的特質融合,由於布崙迪生前操流利英語,梅委斯吃他後認為自己的英文程度立即提升了。
搖滾明星奇思.理查斯(Keith Richards)忍不住在他過世的父親火化後,吸了一下骨灰,感覺將父親的本質吸入體內。還有,人們難以承認的事例,就是廣義基督教的「聖餐」(Eucharist)。如同《約翰福音6:45》寫道:「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恆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作者布倫認為,這根本就是模擬食人的投射,聖餐讓信徒透過儀式,聯想進食基督的身體和血,吸收神聖的特質,十六世紀引起不少神學辯論,認為當中正正顯示了吃人習性。(非宗教的例子,則是「吃胎盤」的文化)
渴求純潔處女,喜歡輕度自虐
當然,飲食的心理投射也不一定只有吃人這麼恐怖,學者透過統計發現,美國人每年花大量金錢購買瓶裝水,比全年花在電影上的錢還多,除了受品牌影響外,更是追求「純粹潔淨」的感覺/本質。[註四] 這種追求純潔的心態,也反映在男人對處女的渴求。曾有位叫納塔莉.迪倫(Natalie Dylan)的女子拍賣自己的「第一次」(童貞),最後有人出價高達一百萬美元。也會有妻子花錢修復處女膜,以此作為禮物贈送給丈夫;而最極端的例子是一些人不知那裏來的迷信,認定跟處女性交可治療愛滋病,令不少少女因此受害。
說到這裏,美中不足的是,雖然布倫在著述中有提及演化史對人心喜惡的影響力,像人類普遍討厭吃蟲和亂倫等等。但總體來說,還未算是書中焦點所在,他傾向強調人類擁有意識能力以後,文化使人類發展出變化多端的喜好,也滿足各種心理投射。又例如,人類看來是唯一愛辣的動物,也喜歡一定程度受苦後,體驗箇中的快感,所以才喜歡一定傷害性的「性虐」(SM)、血腥恐怖片,在大致安全的情境下,結合了尋求虛擬的搏鬥、挑戰本能,換取刺激亢奮。
簡單、擬人化的宗教才多人信
不過,關於演化對人喜惡的心理影響,我們大可從認知科學家吉姆.戴維(Jim Davies)的新著作《吸睛的科學(Riveted)》加以認識。戴維從各種人類演化本能之中,整理出一些影響人心喜惡的重要特質:擬人化、簡單、地位、熟悉、新奇、平均、慰藉等,他除了解釋演化心理外,亦引用不少宗教和外星人的題材加以說明。[註五]
人類古今流傳甚廣的宗教經典,絕大部分內容會透過「擬人化、簡單比喻」來傳播,例如,神/上帝會因為人的善行而「喜悅」,因為人的不忠和惡行而「震怒」等等,這些擬人化的情感,容易叫人加深體會和明白;你甚少聽說,宗教將神描繪成一種抽象的力量,而且難以形容,或稱神由類似數理法則的元素組成,內容完全沒有觸及簡單直接的情感世界。筆者敢斷定,假如現在有兩位教主創立不同的新宗教,一位以大量擬人化和簡單比喻來說明教義,另一位則透過量子物理學來說明,前者必然擁有最多信眾,後者信眾應少得可憐,無論你要筆者下多少賭注都願意。
作者引述心理學家亞當.威茲的研究,發現人們聯想擬人化神靈時,活化的腦區,同樣是負責社交認知的區域。這正正是傑西.貝林(Jesse Bering)在著作《信仰本能(The Psychology of Souls, Destin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中強調,自閉症患者由於失去重要的社交能力,他們思考宗教信仰時,比較認為神是一種規律、法則的力量,而不是那種會跟人類說話,會讚賞和懲罰人類的上帝;這是人類演化出社交和虛擬能力以後,對萬事萬物尋求「解釋」的本能。(大腦對解釋現象過於敏感,極端情況等同「精神分裂症」) [註六] 而社會學家佛列德.普瑞維克認為,女性普遍比男性有更強的社交天賦,所以宗教信仰上,虔誠的女信徒始終較多。
而且,擬人化的聯想,同樣出現在描繪外星人上。心理學家佛德列克.梅姆斯壯指,那些宣稱曾被外星人綁架的團體,他們形容的外星「小灰人」,全身赤裸、大頭、大眼、小嘴,通通都源自模擬女性的特質。更有人利用電腦程式模擬嬰兒眼中女性的樣貌,結果發現就是那些「小灰人」的模樣﹗更甚,聲稱被外星人綁架的故事中,內容大都涉及「性與暴力」,其實一如人類社會的綁架事件。
演化、基因令人更愛陰謀論
戴維認為宗教、神秘事件,簡單而激起情緒的故事最吸引人,使人著迷,背後也跟地位和慰藉息息相關,神靈和外星人都高高在上,如同人類漫長的演化,令我們特別關注高位的領袖,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喜怒哀樂,都關乎自身的安危,慰藉恐懼,帶來希望 。演化使我們很「好奇、八卦」那些影響自己生命的重要人物,可稱為「人際吸引論」,除留意領袖、神靈的指示之外,還包括:敵人、愛人的訊息,難怪,筆者聽聞香港有些辦公室政治,由於競爭,竟天天統計同事於工作時間在臉書(facebook) 貼了多少段留言,轉告上司以攻擊對方。
若撇開演化心理,喜歡迷信宗教、神秘故事的人,也跟遺傳有關。「明尼蘇達雙胞胎研究計劃」發現,愈對宗教虔誠的人,有超過47%受基因影響,家庭影響只佔11%。人類的迷信思維,也反映在陰謀論者身上:不喜歡以證據、理據去解讀事物,傾向新奇的聯想和感覺。
作者指出,陰謀論者寧願相信「美國政府製造出愛滋病毒,藉此殺害同性戀者和黑人」,完全不會思考理據和可能性有多大。一如筆者曾聽說有陰謀論者聲稱,當年香港爆發肺炎「SARS」是中共刻意造成的,希望破壞香港樓市和經濟,大舉引入大陸資金,令筆者非常無奈。值得一提是,曾有學者指出,喜歡陰謀論的人,道德水平也相對低下;這也關乎他們只選取自己喜歡、新奇又簡單易懂的說法來解釋現實,在封閉的團體內,互相傳播熟悉的資訊,減少遭受挑戰;從不重視推理分析、機率大小,只要他們認定存在陰謀,難以被理據說服。
從政者 IQ 不能太高,男女外貌不可太獨特
的確,有一種稱為「知覺流暢性假設」,我們喜歡容易解釋和思考的內容,太複雜艱難的東西無法「入腦」,連支持政治人物的喜好也一樣。心理學家狄恩.賽門頓就「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選舉進行研究,發現成功當選的政治人物,智商都在社會平衡智商的範圍內。例如美國由公民選出總統,計算平均值後,得出總統的智商大約在119;而英國首相由下議院議員選出,由於國會議員平均智商較高,得出首相的智商大約在134。意味大眾喜歡的政治人物,取其外貌與智力平均者勝,太笨令人討厭,太聰明亦不討好,或許跟大眾聽不懂其「偉論」有關。
最後,兩性的吸引力又如何?原來一般而言,不論男女,兩性同樣最注視女人的外貌,亦同樣最注意男人的地位;換句話說,女人外貌比地位重要,男人地位比外貌重要。關於外貌的研究,令人奇怪的是,除了過往有研究指男女喜歡五官「平衡對稱」的樣貌、免疫系統的配合,原來長相也不能過於獨特。戴維表示,平凡的臉孔比較吸引,跟基因遺傳較健康有其相關性;此外,女性擇偶儘管差異較大,她們在排卵期普遍會喜歡與長相粗獷、較具社會優勢的男人建立關係,到了想尋找好丈夫時,就偏向選擇長相斯文、仁慈,重視孩子和勤奮的對象,可謂各有市場。
另外,在閱讀喜好方面,心理學家陶德.夏克福的大型研究表示,男人鍾情「性愛」,女人鍾情「戀愛」,是橫跨三十六種文化的普遍原則。而不論男女,才能也是一種優勢,因為人類創作藝術、運動和表演的能力,是智力的表現,反映演化「性擇」上的優勢,是吸引力的一種,絕非單純由外在美決定,大可放心。
筆者身處的香港社會,大部分人較易受煽情的言論影響,也缺乏求真精神,只要言論簡單、生動,就傾向認同相信,陰謀家利用人性的偏好、思維漏洞謀取利益。但願,上述心理研究,有助知識分子反思價值、重視推理、留意證據,制衡演化與群眾加諸我們喜惡的偏見。
- [註一]保羅.布倫(Paul Bloom)著:《香醇的紅酒比較貴,還是昂貴的紅酒比較香?從食物、性、消費、藝術看人類的選擇偏好,破解快樂背後的行為心理》(How Pleasure Works: the New Science of Why We Like What We Like),臺北市,商周出版,2014年4月。
- [註二]Pearls Before Breakfast: Can one of the nation’s great musicians cut through the fog of a D.C. rush hour? Let’s find out.
- [註三]Operation of the laws of sympathetic magic in disgust and other domains; by Rozin, Paul; Millman, Linda; Nemeroff, Ca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0(4), Apr 1986, 703-712.
- [註四]MESSAGE IN A BOTTLE; by Charles Fishman, 2007.
- [註五]吉姆.戴維斯(Jim Davies)著:《吸睛的科學 — 為什麼八卦、藝術、宗教和恐怖片令人著迷?》(Riveted: The Science of Why Jokes Make Us Laugh, Movies Make Us Cry, and Religion Makes Us Feel One with the Universe),究竟出版,2015年2月。
- [註六]傑西.貝林(Jesse Bering)著:《信仰本能:關於靈魂、命運和人生意義的心理機制》(The Belief Instinct: The Psychology of Souls, Destin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臺北市,啟示出版,2011年9月,p72 – p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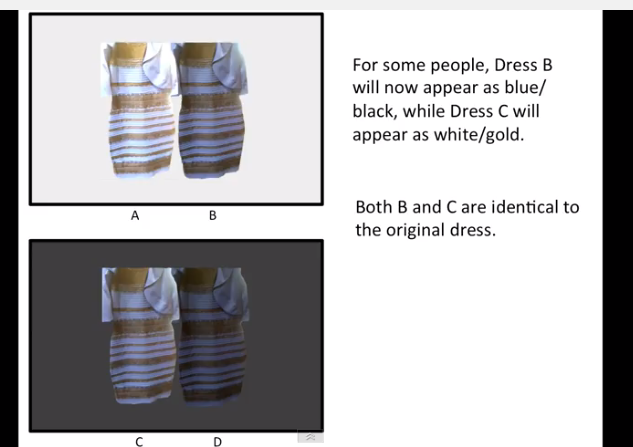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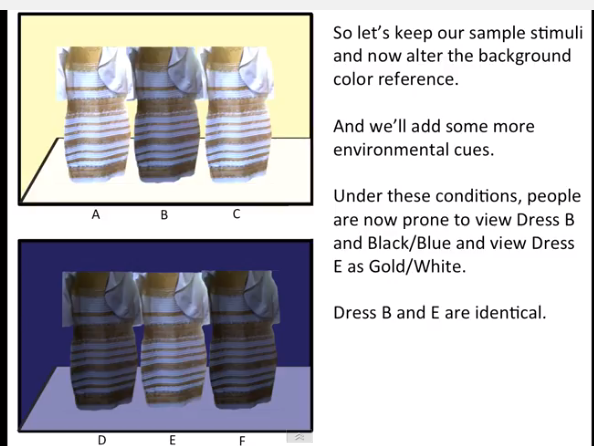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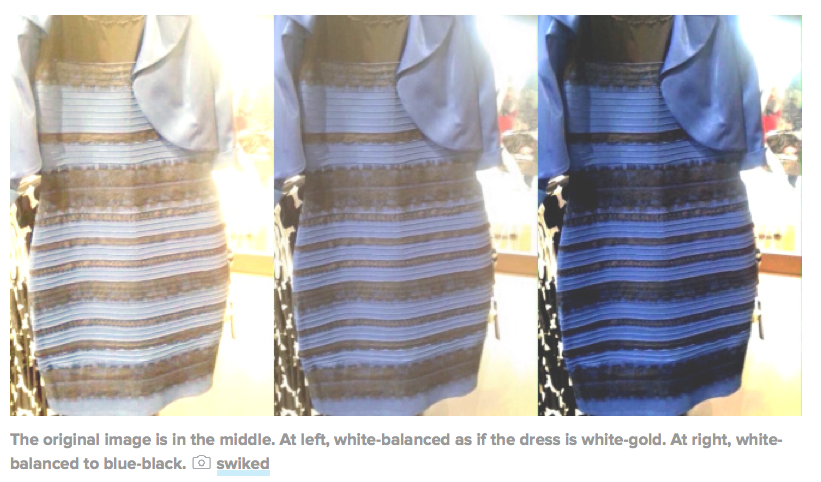


















![圖三、腸胃道微生物的菌相受到宿主的飲食節律的影響 左圖是Bacteroides (屬於腸道微生物)在不同時間的多寡變化。ZT (zeitgeber time)是由實驗室所訂的環境時間: ZT 0 是燈亮的時間點 (light phase); ZT12 是燈熄的時間點 (dark phase)。小鼠是夜行性動物,因此藍色是活動期間進食而紅色則是休息時間進食的腸胃道微生物變化。 [5]](http://pansci.tw/wp-content/uploads/2015/04/p3.png)
![圖四、腸道微生物投射時差對代謝的影響在新的宿主體內 最左圖是該實驗設計的示意圖: 從計畫飛越跨時區的參與者身上,取得時差前 (黑色),經歷時差一天後 (紅色),和時差後14天 (藍色)的糞便採樣,並將該參與者的腸胃道微生物移植到無菌鼠身上。實驗結果顯示,即使無菌鼠是在無時差的正常光照環境下,期待謝功能如體重與血糖調節能力仍然受到所移植的腸胃道微生物的影響。[5]](http://pansci.tw/wp-content/uploads/2015/04/p4-560x456.jpg)















